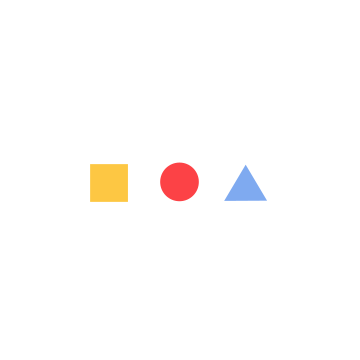王迅:这次演恶人,我扎进去了|新浪蜂鸟|王迅|新浪|蜂鸟
3月19日,北京英皇影城的休息室里,王迅斜倚在沙发上,连轴转的高强度工作让他的嗓音变得沙哑,交流时不得不频频清嗓和喝水,随即会向《新浪蜂鸟》表示出歉意。
在《怒水西流》中,王迅扮演“张晓军”一角,一个残暴的杀人凶手。
这是王迅第一次在大银幕上演“纯粹的恶人”。提到角色张晓军时,他有些激动:“对,有点变态!”
他为此写了丰富的人物小传,在开拍前他曾将其中虚构的部分与主创团队进行过一次沟通。
编剧兼导演冯勇沁告诉他,这些就是剧本装不下但应该有的部分。
在王迅的理解中,这个变态的凶手,一方面感受着“极致”的亲情,一方面又经历过极致的恶,在这两种情感的冲撞下,最终让他走向了无法控制的黑暗……
《怒水西流》的拍摄地点在重庆,和让他成名的电影《疯狂的石头》拍摄地点在同一个地方。但在这部戏中,他不再操着浓重的方言,以“丑角”的形式登场。
对于喜剧这个赛道,他说“可能是一开始让观众认识到我的一个路径,但是它并不是我唯一的路径。”
(以下为对话过程,《新浪蜂鸟》简称“蜂鸟”)
蜂鸟:《怒水西流》这个戏里边的角色挺复杂的。首先他(张晓军)的一个身份是儿子,我能看到他有一些天真的部分,另一方面他有一些很愤怒、无法控制的部分。当时准备这个角色的时候,有没有参考一些其他的角色?
王迅:
没有,说实话因为我平常的创作习惯,不是接了一个什么本,就在我所看过的电影里边搜索有哪种类似的人物,把他“抓”过来,这是一种创作方法。但是我的创作方法是,就剧作提供的这个人物,去深挖。因为张晓军这个人物,刺激起了我创作的欲望。我看完之后就跟导演聊,这样的一个人物,他究竟经历了什么?
这个角色呈现出来的是极度的恶,里边一些台词都太不正常了。那我必须要把这个人物,整个给解构清楚。后来我就开始顺着导演提供的一些设定,给这个人物写了一个很丰富的人物小传,包括他耳朵究竟是怎么受的伤?他被他爸爸打,什么情况下被他爸爸打的?他爸爸是个什么样的人物?只有这样,你才能看到现在张晓军的一个状态。
张晓军其实就是经历了极致的恶,然后又经受了极致的爱,这两股没法调和的力量给他拧巴成了这样。其实是一个家暴男,造成了这个家所有的恶。但他爸爸在这个戏里边一点都没出现,只是出现在言语之间。但实际上是他爸爸的家暴,他爸爸打他妈妈,然后张晓军挺身而出保护他妈妈,一次、两次、三次。
蜂鸟:这是不是也是你第一次演一个纯粹的恶的角色?他身上有令人同情的部分、病态的部分,但唯独没有你过往角色里诙谐的部分。
王迅:
对,原来我演过很多坏人,但这些坏人都是用“坏”包裹的一些喜剧人物,其实没有那么深入到人物的内心,这次这个角色是完全扎进去了。我希望观众能够看到一些他曾经的不堪,可能他这种人不能被原谅,但是你得知道原因是什么。
当然这不是这个戏里去解决的,这是电影留给观众的一个思考。你看他被他爸爸打成这样,他妈妈又用一种更加变态的极致的爱,把他这么大个人保护起来。
蜂鸟:你拖着身子行进的那场戏,感觉有些像一些恐怖片或恐怖游戏中的反派形态,对于那个姿态你有参考过其他的一些作品吗?
王迅:
那个是因为我当时在猪场体验生活,看了很多他们的状态。他们干活不像我们想象地忙忙叨叨,他是悠悠哉哉地、整体在那里晃的那种感觉,我就觉得放在这个人物身上特别合适。
在那个猪场里边,你知道吗?管理猪场的这个人其实就是整个猪场的主人,这一片就是他的天地。任何一头猪,最后都是要被他杀掉的。我觉得导演给这个人物设计的工作环境特别好。包括他一上场,给猪断尾,这其实是很残忍的一个事儿,他用这个方式来铺垫这个人物,瞬间就完成了。
蜂鸟:这部电影的拍摄地是在重庆,重庆跟您几个作品都有关,从《疯狂的石头》到《怒水西流》,再次回到重庆拍摄有什么不一样的感受?
王迅:
说实话,重庆肯定是我的福地,也是我的家乡,因为我妈妈是重庆人,那方水土太熟悉了。但这部作品好像是我为数不多的在重庆拍摄但是没说重庆话的电影。
当时有说想采用方言,让整个故事和环境更加贴合,但后来导演说,其实应该让观众把更多的(注意力)聚焦到这个家庭,就放弃掉它(和重庆的联系)。所以后来我们就没有用方言,全部都是用普通话来完成的。但是电影里边传递出来的还是西南的那种感觉,那种迷雾重重的那种状态。
蜂鸟:不用方言在重庆拍电影,这是你成长的一部分吗?
王迅:
我觉得方言,是绝对能够帮助你去塑造人物的。到现在为止,我坦言,我用方言演戏和用普通话演戏绝对是两种状态。不是压力问题,而是你的(角色)那个精彩度,用方言会提升不少。你驾驭”母语”的时候,整个神态都不一样,演员的节奏都不一样。
当《疯狂的石头》火了之后,后来好多戏里边我都用四川话去演绎,然后渐渐地会发现,你自己其实是想有所突破的。我曾经有一个特别好的战友,现在也是一个导演,他就问过这个问题,他说我为什么演戏老用方言?我说好用啊,我抓不住人物的时候,我用那个(方言),马上就觉得人物的状态附在了身上。他说你还是应该用普通话,你再这样下去,今后这个优势就会成你的一个局限。
所以后来我就开始尝试,完全甩掉方言,就是用普通话,能不用方言的时候都不用。有时候很多导演他会给你定位,“王老师你就用那个方言”,我说别用太多了。演员,用普通话不会给你定性,但你用方言渐渐就会给你定性,但凡有一次不一样就觉得别扭。我其实因为这个事儿还别扭了很长时间,演着演着总觉得哪个词跟不上。用方言的时候你绝对没有词跟不上,很多时候还会冒出一些你自己都想不到的词,这就是之前很长一段时间,我在转换(语言)的时候的一个过程。这两年应该好很多了。
蜂鸟:看起来就是说两种方言的区别,但实际上是一个人自信心的变化,他敢不敢拥抱变化?
蜂鸟:现在的你在拍戏方面是自信的吗?
王迅:
其实我在拍戏这方面一直是有信心的,这个信心来自于我对角色的充分准备。我在片场的时候有一个习惯,就是我身边的工作人员都知道,我绝不可能到现场现看剧本,现在那琢磨词儿,我都是提前想好了。尤其是(拍)电影,这个人物全在我脑子里边,一定的。我必须要装得很满,我演的时候才会有(信心),这是我对我自己的一个要求,这么多年都是如此,所以到现场我是自信的。
我过去不自信是在于哪儿呢?在于有些对手演员到现场之后会说:这场戏我想这么这么演,我心想这跟我设想的情景好像不太一样,那个时候就会不自信。
蜂鸟:你会尝试解释或说出自己的想法吗?
王迅:
不能演在一起不用解释,对方如果是个明白演员,大家只要一搭手演起来,就会觉得这事不对,得坐下来聊一聊。因为这个戏不是说你一个人好就整个就是好的,需要互相配合的,必须得是对手之间能接得上的。
我们原来接受到的(教育)都是演戏是为对手演,你把该给的肩膀给到、该给的尺寸给到,那对手演起来就会舒服,他也能在你肩膀头上再往上翻,那这个戏就要往上涨了。所以很多时候说飙戏不是飙戏,它是涨戏,互相往上涨。而不是说你演得这么好,我就必须要演过你,那就傻了。
蜂鸟:碰到比你更资深的合作演员,如果碰到这种情况,你还是沉默的时候多一些吗?
王迅:
碰到比我资深的合作演员,他们的想法有时候确实比我好,我会很服气地虚心接受的。但如果对想法有分歧,我们也会去提,不会不提的。因为在戏上,真正的演员是不会说我完全都听你的,这两个人物如何交融在一起是重要的。
蜂鸟:这与你成长过程中对于权威的记忆有关吗?
王迅:
肯定会的。因为我过往的人生经历,会有一种集体无意识的东西在身上,包括对于权威。其实这个对权威(的服从)还不是说单位带给你的,我觉得是我父亲带给我的。
因为(小时候的我)太调皮了,确实调皮。到了部队后,整个人可能也懂事了,得按规矩来,得讲秩序,任何一个事都不能说完全按照自己的想法去折腾,渐渐地你又形成了另外的一种思维状态,就进入了另外的一种感觉。
蜂鸟:你今年已经50岁了,知天命了,未来对于与权威的关系,还会发生变化吗?会回到儿童时那个更大胆、直接的状态吗?
王迅:
我觉得无所谓喜不喜欢,这就是我目前的一个状态,你长到这个状态了,他是有他的原因的。就像我们去设计每一个人物一样,他得有他的过往的经历,我恰恰有我前面丰富的人生经历。我骨子里肯定有我小时候最初的那个敢想敢干(的模样),但是也有边界、有规矩、该服从,要顾全大局,这是肯定的。
我觉得无所谓这种状态是好还是不好,这就是目前的我。可能在有一天,我忽然又回到了小时候那种混不吝的状态。但是那一天的混不吝,肯定和你小时候最初不懂事的那个混不吝又完全不一样了。道德经里有一句话叫“复归于婴儿”,我们有一天可能也会“复归于婴儿”。
蜂鸟:你之前很长一段时间以喜剧配角的身份被大家认识,如果这一条路再往前走,它的终点应该是什么样的?
王迅:
我没想过。说实话我还是一个比较脚踏实地的人,不愿意去说这个事儿。我希望每天很努力地往前走,至于走到哪一步,它就是哪一步。有的人刚走两步就踩到了一个弹簧,咵就上去了;有的人就咔嚓踩到一个坑。这个我觉得很正常。我没有去给自己设立(目标),包括喜剧这条路,这个赛道可能是一开始让观众认识到我的一个路径,但是它并不是我唯一的路径。包括现在演《怒水西流》,我也希望是能不断拓宽自己。
其实每次电影路演,都会被问到“你希望挑战什么样的角色?”之类的问题。我会回答:演员首先一点,在我们目前这个程度,还不敢说我想挑战哪个就挑战哪个,因为演员都面临着被别人选择。但是从我内心来说,无论什么样的角色我都是希望自己能够去演的,能够把他在导演或者编剧的基础上给他稍微加一点分,或者说不减分地去完成,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演员的本分。至于你能达到多少?那个东西是和你的修为以及机缘共同产生下,才有可能出现的东西。
蜂鸟:好莱坞有一个演员叫金·凯瑞,我们也能看到一个喜剧出身的演员,最后总有一些悲伤的部分想要表达。
王迅:
喜剧说实话是我觉得最难演的,不是说我们演喜剧才这么说,因为喜剧演员是两个脑袋演戏。他不像演正剧,可以完全投入。演张晓军的时候我是完全把自己融到这个人物里了,我那一段时间心里边想的都是(张晓军),你必须让自己要有那个人物的状态,你得有那个劲,人就是要往里沉,他才能扎得比较深。
喜剧演员相对来说扎得比较浅一些,但是喜剧演员的难度在于两个脑袋:一个脑袋控制角色,一个脑袋控制演员,我本身还得想这个包袱够不够响。你得琢磨观众,这个地方我到底该怎么说,该怎么把握表演的尺寸、节奏,不是能很轻易地纯粹地投入进去的,所以说演喜剧是很难的。
而且喜剧演员有时候演起来没那么过瘾。话剧的喜剧演员是过瘾的,他是能和观众直接交流的。拍电影或电视剧的时候,这个包袱是要到最后剪完了观众才会有反馈的,在现场拍摄的时候你不会立刻知道,可能也就是现场的工作人员乐一乐,挺难受的。
蜂鸟:像《怒水西流》这样的作品,会给你带来一种不安全感吗?比如会担心以后再难遇到这类的作品或者是转型之后,会对其他的选择有一些新的焦虑吗?
王迅:
其实都是缘分。我们有错过很多戏,后来人家上映的时候说“哎呀当时应该去呀”,但这个东西就是你的命。你演了这个戏,你跟这个角色之间,你俩是有缘分的。你能够去呈现它,能够把它塑造出来,这就是一个很好的过程了。
至于今后能演什么,或者还有没有超越他的角色。不好说。
3月19日,北京英皇影城的休息室里,王迅斜倚在沙发上,连轴转的高强度工作让他的嗓音变得沙哑,交流时不得不频频清嗓和喝水,随即会向《新浪蜂鸟》表示出歉意。
在《怒水西流》中,王迅扮演“张晓军”一角,一个残暴的杀人凶手。
这是王迅第一次在大银幕上演“纯粹的恶人”。提到角色张晓军时,他有些激动:“对,有点变态!”
他为此写了丰富的人物小传,在开拍前他曾将其中虚构的部分与主创团队进行过一次沟通。
编剧兼导演冯勇沁告诉他,这些就是剧本装不下但应该有的部分。
在王迅的理解中,这个变态的凶手,一方面感受着“极致”的亲情,一方面又经历过极致的恶,在这两种情感的冲撞下,最终让他走向了无法控制的黑暗……
《怒水西流》的拍摄地点在重庆,和让他成名的电影《疯狂的石头》拍摄地点在同一个地方。但在这部戏中,他不再操着浓重的方言,以“丑角”的形式登场。
对于喜剧这个赛道,他说“可能是一开始让观众认识到我的一个路径,但是它并不是我唯一的路径。”
(以下为对话过程,《新浪蜂鸟》简称“蜂鸟”)
蜂鸟:《怒水西流》这个戏里边的角色挺复杂的。首先他(张晓军)的一个身份是儿子,我能看到他有一些天真的部分,另一方面他有一些很愤怒、无法控制的部分。当时准备这个角色的时候,有没有参考一些其他的角色?
王迅:
没有,说实话因为我平常的创作习惯,不是接了一个什么本,就在我所看过的电影里边搜索有哪种类似的人物,把他“抓”过来,这是一种创作方法。但是我的创作方法是,就剧作提供的这个人物,去深挖。因为张晓军这个人物,刺激起了我创作的欲望。我看完之后就跟导演聊,这样的一个人物,他究竟经历了什么?
这个角色呈现出来的是极度的恶,里边一些台词都太不正常了。那我必须要把这个人物,整个给解构清楚。后来我就开始顺着导演提供的一些设定,给这个人物写了一个很丰富的人物小传,包括他耳朵究竟是怎么受的伤?他被他爸爸打,什么情况下被他爸爸打的?他爸爸是个什么样的人物?只有这样,你才能看到现在张晓军的一个状态。
张晓军其实就是经历了极致的恶,然后又经受了极致的爱,这两股没法调和的力量给他拧巴成了这样。其实是一个家暴男,造成了这个家所有的恶。但他爸爸在这个戏里边一点都没出现,只是出现在言语之间。但实际上是他爸爸的家暴,他爸爸打他妈妈,然后张晓军挺身而出保护他妈妈,一次、两次、三次。
蜂鸟:这是不是也是你第一次演一个纯粹的恶的角色?他身上有令人同情的部分、病态的部分,但唯独没有你过往角色里诙谐的部分。
王迅:
对,原来我演过很多坏人,但这些坏人都是用“坏”包裹的一些喜剧人物,其实没有那么深入到人物的内心,这次这个角色是完全扎进去了。我希望观众能够看到一些他曾经的不堪,可能他这种人不能被原谅,但是你得知道原因是什么。
当然这不是这个戏里去解决的,这是电影留给观众的一个思考。你看他被他爸爸打成这样,他妈妈又用一种更加变态的极致的爱,把他这么大个人保护起来。
蜂鸟:你拖着身子行进的那场戏,感觉有些像一些恐怖片或恐怖游戏中的反派形态,对于那个姿态你有参考过其他的一些作品吗?
王迅:
那个是因为我当时在猪场体验生活,看了很多他们的状态。他们干活不像我们想象地忙忙叨叨,他是悠悠哉哉地、整体在那里晃的那种感觉,我就觉得放在这个人物身上特别合适。
在那个猪场里边,你知道吗?管理猪场的这个人其实就是整个猪场的主人,这一片就是他的天地。任何一头猪,最后都是要被他杀掉的。我觉得导演给这个人物设计的工作环境特别好。包括他一上场,给猪断尾,这其实是很残忍的一个事儿,他用这个方式来铺垫这个人物,瞬间就完成了。
蜂鸟:这部电影的拍摄地是在重庆,重庆跟您几个作品都有关,从《疯狂的石头》到《怒水西流》,再次回到重庆拍摄有什么不一样的感受?
王迅:
说实话,重庆肯定是我的福地,也是我的家乡,因为我妈妈是重庆人,那方水土太熟悉了。但这部作品好像是我为数不多的在重庆拍摄但是没说重庆话的电影。
当时有说想采用方言,让整个故事和环境更加贴合,但后来导演说,其实应该让观众把更多的(注意力)聚焦到这个家庭,就放弃掉它(和重庆的联系)。所以后来我们就没有用方言,全部都是用普通话来完成的。但是电影里边传递出来的还是西南的那种感觉,那种迷雾重重的那种状态。
蜂鸟:不用方言在重庆拍电影,这是你成长的一部分吗?
王迅:
我觉得方言,是绝对能够帮助你去塑造人物的。到现在为止,我坦言,我用方言演戏和用普通话演戏绝对是两种状态。不是压力问题,而是你的(角色)那个精彩度,用方言会提升不少。你驾驭”母语”的时候,整个神态都不一样,演员的节奏都不一样。
当《疯狂的石头》火了之后,后来好多戏里边我都用四川话去演绎,然后渐渐地会发现,你自己其实是想有所突破的。我曾经有一个特别好的战友,现在也是一个导演,他就问过这个问题,他说我为什么演戏老用方言?我说好用啊,我抓不住人物的时候,我用那个(方言),马上就觉得人物的状态附在了身上。他说你还是应该用普通话,你再这样下去,今后这个优势就会成你的一个局限。
所以后来我就开始尝试,完全甩掉方言,就是用普通话,能不用方言的时候都不用。有时候很多导演他会给你定位,“王老师你就用那个方言”,我说别用太多了。演员,用普通话不会给你定性,但你用方言渐渐就会给你定性,但凡有一次不一样就觉得别扭。我其实因为这个事儿还别扭了很长时间,演着演着总觉得哪个词跟不上。用方言的时候你绝对没有词跟不上,很多时候还会冒出一些你自己都想不到的词,这就是之前很长一段时间,我在转换(语言)的时候的一个过程。这两年应该好很多了。
蜂鸟:看起来就是说两种方言的区别,但实际上是一个人自信心的变化,他敢不敢拥抱变化?
蜂鸟:现在的你在拍戏方面是自信的吗?
王迅:
其实我在拍戏这方面一直是有信心的,这个信心来自于我对角色的充分准备。我在片场的时候有一个习惯,就是我身边的工作人员都知道,我绝不可能到现场现看剧本,现在那琢磨词儿,我都是提前想好了。尤其是(拍)电影,这个人物全在我脑子里边,一定的。我必须要装得很满,我演的时候才会有(信心),这是我对我自己的一个要求,这么多年都是如此,所以到现场我是自信的。
我过去不自信是在于哪儿呢?在于有些对手演员到现场之后会说:这场戏我想这么这么演,我心想这跟我设想的情景好像不太一样,那个时候就会不自信。
蜂鸟:你会尝试解释或说出自己的想法吗?
王迅:
不能演在一起不用解释,对方如果是个明白演员,大家只要一搭手演起来,就会觉得这事不对,得坐下来聊一聊。因为这个戏不是说你一个人好就整个就是好的,需要互相配合的,必须得是对手之间能接得上的。
我们原来接受到的(教育)都是演戏是为对手演,你把该给的肩膀给到、该给的尺寸给到,那对手演起来就会舒服,他也能在你肩膀头上再往上翻,那这个戏就要往上涨了。所以很多时候说飙戏不是飙戏,它是涨戏,互相往上涨。而不是说你演得这么好,我就必须要演过你,那就傻了。
蜂鸟:碰到比你更资深的合作演员,如果碰到这种情况,你还是沉默的时候多一些吗?
王迅:
碰到比我资深的合作演员,他们的想法有时候确实比我好,我会很服气地虚心接受的。但如果对想法有分歧,我们也会去提,不会不提的。因为在戏上,真正的演员是不会说我完全都听你的,这两个人物如何交融在一起是重要的。
蜂鸟:这与你成长过程中对于权威的记忆有关吗?
王迅:
肯定会的。因为我过往的人生经历,会有一种集体无意识的东西在身上,包括对于权威。其实这个对权威(的服从)还不是说单位带给你的,我觉得是我父亲带给我的。
因为(小时候的我)太调皮了,确实调皮。到了部队后,整个人可能也懂事了,得按规矩来,得讲秩序,任何一个事都不能说完全按照自己的想法去折腾,渐渐地你又形成了另外的一种思维状态,就进入了另外的一种感觉。
蜂鸟:你今年已经50岁了,知天命了,未来对于与权威的关系,还会发生变化吗?会回到儿童时那个更大胆、直接的状态吗?
王迅:
我觉得无所谓喜不喜欢,这就是我目前的一个状态,你长到这个状态了,他是有他的原因的。就像我们去设计每一个人物一样,他得有他的过往的经历,我恰恰有我前面丰富的人生经历。我骨子里肯定有我小时候最初的那个敢想敢干(的模样),但是也有边界、有规矩、该服从,要顾全大局,这是肯定的。
我觉得无所谓这种状态是好还是不好,这就是目前的我。可能在有一天,我忽然又回到了小时候那种混不吝的状态。但是那一天的混不吝,肯定和你小时候最初不懂事的那个混不吝又完全不一样了。道德经里有一句话叫“复归于婴儿”,我们有一天可能也会“复归于婴儿”。
蜂鸟:你之前很长一段时间以喜剧配角的身份被大家认识,如果这一条路再往前走,它的终点应该是什么样的?
王迅:
我没想过。说实话我还是一个比较脚踏实地的人,不愿意去说这个事儿。我希望每天很努力地往前走,至于走到哪一步,它就是哪一步。有的人刚走两步就踩到了一个弹簧,咵就上去了;有的人就咔嚓踩到一个坑。这个我觉得很正常。我没有去给自己设立(目标),包括喜剧这条路,这个赛道可能是一开始让观众认识到我的一个路径,但是它并不是我唯一的路径。包括现在演《怒水西流》,我也希望是能不断拓宽自己。
其实每次电影路演,都会被问到“你希望挑战什么样的角色?”之类的问题。我会回答:演员首先一点,在我们目前这个程度,还不敢说我想挑战哪个就挑战哪个,因为演员都面临着被别人选择。但是从我内心来说,无论什么样的角色我都是希望自己能够去演的,能够把他在导演或者编剧的基础上给他稍微加一点分,或者说不减分地去完成,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演员的本分。至于你能达到多少?那个东西是和你的修为以及机缘共同产生下,才有可能出现的东西。
蜂鸟:好莱坞有一个演员叫金·凯瑞,我们也能看到一个喜剧出身的演员,最后总有一些悲伤的部分想要表达。
王迅:
喜剧说实话是我觉得最难演的,不是说我们演喜剧才这么说,因为喜剧演员是两个脑袋演戏。他不像演正剧,可以完全投入。演张晓军的时候我是完全把自己融到这个人物里了,我那一段时间心里边想的都是(张晓军),你必须让自己要有那个人物的状态,你得有那个劲,人就是要往里沉,他才能扎得比较深。
喜剧演员相对来说扎得比较浅一些,但是喜剧演员的难度在于两个脑袋:一个脑袋控制角色,一个脑袋控制演员,我本身还得想这个包袱够不够响。你得琢磨观众,这个地方我到底该怎么说,该怎么把握表演的尺寸、节奏,不是能很轻易地纯粹地投入进去的,所以说演喜剧是很难的。
而且喜剧演员有时候演起来没那么过瘾。话剧的喜剧演员是过瘾的,他是能和观众直接交流的。拍电影或电视剧的时候,这个包袱是要到最后剪完了观众才会有反馈的,在现场拍摄的时候你不会立刻知道,可能也就是现场的工作人员乐一乐,挺难受的。
蜂鸟:像《怒水西流》这样的作品,会给你带来一种不安全感吗?比如会担心以后再难遇到这类的作品或者是转型之后,会对其他的选择有一些新的焦虑吗?
王迅:
其实都是缘分。我们有错过很多戏,后来人家上映的时候说“哎呀当时应该去呀”,但这个东西就是你的命。你演了这个戏,你跟这个角色之间,你俩是有缘分的。你能够去呈现它,能够把它塑造出来,这就是一个很好的过程了。
至于今后能演什么,或者还有没有超越他的角色。不好说。
本文地址: http://www.2345u.cn/article/34.html